散文:夏季的夜晚(杨广虎)
我喜欢安静,不爱动弹,是一个典型的“冬眠动物”,喜欢冬季,不爱夏季;西安的夏季太热,有“火炉”之称,加之,近年来高楼不停拔地而起,关中平原上全种满了“齐刷刷的韭菜高楼”,密不透风,水也泼不进去。生活在这座千年帝都的人,夏季真是有点遭罪了,街道上经常可以看见裸露上身的“膀爷”,大汗淋漓,有不太雅观之嫌,但也能理解,豪爽的陕西楞娃,在与天地争斗,释放着夏天的热情。
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关中西府农村夏季夜晚。麦场里堆满了鼓鼓的化肥袋子,那里面是当年新打的麦子。拉个架子车,把车辕绑在树上或者麦袋上,就可以当做睡觉的“床”了。农村责任制承包到户,每家男人一方面看麦子,一方面享受贾村塬上的凉风。看麦子,全是青壮年男人,老年人、女人和小孩子是不让晚上在外面睡的,全部睡在家里的炕上;据说晚上阴气重,只有青壮年男人的阳气才可压倒。好在当年农村治安很好,熟人社会,没有见过什么偷麦子的“贼娃子”。我已经十几岁了,算是半拉子小伙,可以在夏天的晚上,睡在外边。塬上本来不太热,就是呆在屋里有点闷;睡在架子车上,铺上个麻袋,支上两块砖头,仰望星空,星光闪耀,月光皎洁,闻着麦香,凉风习习,肚子上什么也不盖,累了一天,劳累不堪,心满意足,呼呼大睡。
真是来了“贼”,别说偷麦子,就是把我自己拉走贩卖,都不知道;还是年轻身体强壮,睡得太熟,太美了,太“歘活”了,早上一抹嘴边,口水一片。那时候的人,真是心地善良、诚实、单纯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简单的“丰收”,先把肚子吃饱。“关中妇女多勤俭,上炕剪子下炕镰刀”。的确如此,大家把劳动看做一件日常美好的事情,从来没有觉得劳累或者有些自卑的感觉。
生产队的牛房在土窑洞,我还睡过。窑洞“冬暖夏凉”,我睡在窑洞里的炕上,老黄牛就在旁边,放屁拉屎声音很大而且味道很重,屁股直对着炕头,但丝毫不影响我的睡眠,一睡到底。
上了中学,睡大通铺嫌热,我曾经睡到校园的水泥坐凳上,被老师发现,劝了回去。到了西安,夏季热得不行,弄啥事都没心情,没有空调,大学校园里一对对情侣也不嫌热手拉手往黑乎乎的树林草坪里钻,辛苦了那些老师拿着手电筒汗流浃背四处搜寻,玩着“猫捉老鼠的游戏”。我是穷光蛋、从农村而来发育迟缓,对男欢女爱懵懵懂懂,不受女同学招惹。记得我和丁福升两个人弄了一张凉席,偷偷睡到教院的六层楼顶上,天上黑乎乎的,看不到星星和月亮,没有想到,楼顶晒了一天,被太阳烤的热乎乎,睡在上面,跟冬季的热炕差不多,身子底下是热的,肚子上面吹着风,冰火两重天,蚊子叮的人睡不着,到了早上,才迷迷糊糊睡一会儿。
后来,在秦岭终南山二十年,夏季的晚上,还需要盖上被子,才能睡觉。山里,确实是避暑的好地方,就是阴湿发潮,慢慢地到了一定年龄,关节炎、腰椎间盘突出,这些病随之来了。有人说,终南山是月亮和星星睡觉的地方,安安静静,连植物的呼吸都能听到,天籁之音呀!有时候,我都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现在,睡在有空调、有新风系统的家中,早上起来,满嘴苦涩,身心疲惫,我实在有点难受,严重影响睡眠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得了鼻炎,冷热交替、鼻子堵塞。我宁愿关了空调,一个人睡在书房,热得翻来覆去、大汗淋漓,也不愿意吹空调的冷风。特别是,到了沿海,说什么去度假,空气中黏糊糊的,一天身子都是湿的,不美,不习惯,根子里就是喜欢干燥辽阔的北方。
在热浪滚滚的夏季中,睡在城市的高楼上,我就想到了故乡,干爽利落、吹着自然之风的夜晚,咬上一根甜甜的麦秆,一副满意的“嘴脸”。现在已经在城里扎根了,故乡回不去了,那只是昨日的纪念,也不是什么矫情,我只想留一点自己心底最真实的记录。这记录,如同一张底板,铭刻了人生的苦乐。
2020年7月3日匆于长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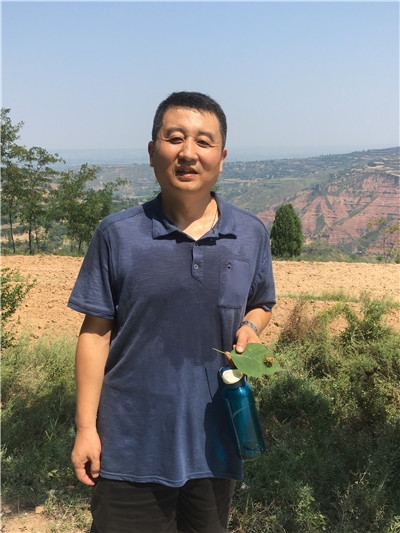
作者杨广虎,男,74年生于陈仓,89年公开发表小说和诗歌。著有历史长篇小说《党崇雅·明末清初三十年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天子坡》《南山·风景》,评论集《终南漫笔》,诗歌集《天籁南山》等。获得西安文学奖、首届中国校园诗歌大赛一等奖、第五届冰心散文奖·理论奖,第三届陕西文艺评论奖、首届陕西报告文学奖、全国徐霞客游记散文大赛奖、中华宝石文学奖等。1996年—2016年在秦岭终南山生活。
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等。
| 感动 | 同情 | 无聊 | 愤怒 | 搞笑 | 难过 | 高兴 | 路过 |
- 上一篇:散文:大地的风景(杨广虎)
- 下一篇:小说:在路上(杨广虎)
相关文章
-
没有相关内容